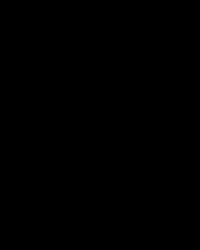52小说网>鱼玄机传 > 结案(第1页)
结案(第1页)
再说温庭筠回到长安旧宅,虽风尘仆仆,眉宇间却有一种尘埃落定的平静。他即刻唤来了一双儿女——温珏与温湘儿。
书房内,一切如旧,"父亲,玄机师妹之事。。。。。。"温珏率先开口,语气沉稳,"京兆府那边已打点妥当,师妹在狱中并未受苦。杜老大人、郑夫人等处也已发力,眼下情势正在好转,父亲不必过于忧心。"
温庭筠微微颔首,目光扫过儿子,又落在女儿脸上,缓缓道:"你们做得很好。为父此番回来,并非不信任你们,而是。。。。。。有些事,需得我亲自面对。"
他顿了顿,声音不高,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力度:"今日唤你们来,是有一事要告知你们。"
他看向温珏,又看向湘儿,眼神坚定:"待玄机出狱,身体调养妥当后,我打算。。。。。。带她往岭南隐居。"
此言一出,温珏与湘儿俱是一怔。湘儿更是脱口而出:"爹爹!您要带玄机姐姐去岭南?那。。。。。。那里山高路远。。。。。。"
温庭筠抬手,止住了女儿未尽的话语。他目光深远,仿佛穿透了眼前的烛火,望见了岭南的青山绿水。
"珏儿,湘儿,"他的声音带着一种罕见的、卸下重负后的疲惫与释然,"为父这一生,拘于礼法,困于声名,看似洒脱,实则怯懦。对你们母亲。。。。。。我自问无愧于心,举案齐眉,相伴半生。然则,正是这份无愧,更让我看清了过往的有憾。"
他深吸一口气:"幼薇那孩子。。。。。。。她灵慧,孤洁,她于学问上的悟性,乃至那份不为人知的脆弱与倔强。。。。。。与我,是同一类人。我曾以为,将她推出去,寻一个如李亿那般看似平顺的归宿,便是对她最好。如今看来,大错特错!那不过是我的懦弱,亦是我不敢直面的本心。"
他的声音里带上了痛楚与悔恨:"若非我一次次退缩,她何至于被逼入道观,乃至今日身陷囹圄?柳芊芊前车之鉴犹在眼前!我不能再。。。。。。不能再眼睁睁看着她独自飘零,重蹈覆辙!"
温珏沉默着,他比湘儿更早察觉到父亲与玄机之间那非同寻常的牵绊,也更理解父亲此刻的决绝。他沉声道:"父亲,岭南湿热,与长安气候迥异,。。。。。。"
"岭南又如何?"温庭筠轻笑一声,那笑声里满是不屑,"我温飞卿半生狂名,何曾真正在意过那些?以往种种顾忌,不过是。。。。。。画地为牢罢了。岭南虽远,却可远离这是非之地。那里四季如春,草木繁盛,正是重新开始的好去处。幼薇需要一处真正清净的天地疗愈身心,而我,也厌倦了这长安城的倾轧纷争。"
他看向一双儿女,目光变得柔和而充满歉意:"只是如此一来,长安家中,便要辛苦珏儿你多担待。湘儿已出嫁,有景修照拂,我尚可放心。你们。。。。。。可能明白为父之心?"
温湘儿早已泪流满面,她扑到父亲身边,抓住他的手臂,哽咽道:"爹爹,女儿明白!女儿都明白!只要您和玄机姐姐能安好,能快活,女儿。。。。。。女儿支持您!"
温珏亦起身,对着父亲深深一揖:"父亲既已决意,儿子自当遵从。长安一切,有儿子在,父亲无需挂心。只望父亲与师妹。。。。。。在岭南,一切安好。"
温庭筠看着眼前已然长大成人、明理懂事的一双儿女,眼中终是泛起一丝湿意。他伸出手,轻轻拍了拍儿子的肩膀,又抚了抚女儿的头发。
"如此。。。。。。我便安心了。"
窗外,夜色深沉。一条艰难却坚定的路,已在温庭筠脚下清晰展开,路的尽头,是岭南的暖阳,和一个等待他携手同归的身影。
一月后,皇帝在权衡利弊后,做出了那个必然的决定。他颁下的口谕,用"文笔可观"肯定了士林与文坛的呼声,然"言辞或有激烈"但终"念其女流,心存社稷,无罪释放"的体现了皇室的"宽仁"。
稍作停顿后,皇帝又补充道:"既已证明清白,着即免除道籍,复归良民。"为这场风波画上了一个各方都能接受的句点。
再说玄机,京兆府大牢的三个月,因着温珏的暗中打点,虽免了刑讯之苦,但那无边的孤寂与漫长的等待,本身就是一种酷刑。然玄机深知,既身陷囹圄,无力改变外物,唯有向内探寻。
她想起很多年前,教坊的雕梁画栋下,那个垫脚想偷拿糕点的小女孩。是柳芊芊将桂花糕塞给她,低声道:“玄机,拿着。”那点甜意,是她灰暗童年里为数不多的暖色。后来,柳芊芊腕上那道为拒客留下的浅疤,成了她心中关于“刚烈”最初的定义。
她想起初入温府,先生将那本《昭明文选》递到她手中,目光认真:“学问之道,无分男女,唯有勤勉与真心。”想起师娘的一盏杏仁茶,以及轻声的安慰“幼薇,慢慢来”,熨帖着她敏感不安的心。想起湘儿,那个活泼娇憨的妹妹,她们课后一同偷摘枇杷,夏夜并肩数星星,那是她沉重课业外最鲜亮的色彩。
她想起李亿,那个曾许她“揽月入怀”的状元郎。红烛下的炽热告白,裴氏刁难时的“暂且忍耐”,柳芊芊蒙冤时的“权宜之计”,那些爱与恨,信任与背叛,在她心上烙下最深的刻痕。
她想起咸宜观中“诗词候教”的木牌,郑夫人的智慧提点,以及西行路上敦煌飞天的绚烂、《西行漫记》笔下的万里山河。
靠着这些回溯,她熬过了狱中漫长日夜。
天启十一年二月玄机被释放,风波暂平。
然皇帝并未将此事轻轻放过。他深知“谤讪”之论绝不会空穴来风,背后必有推波助澜之手。那本《西行漫记》他亦粗略翻过,文辞见识确属上乘,其中忧国忧民之思,与杜老大人、郑姑母所言并无二致。如此才女,竟险些殒命于狱中,若非几方力量及时制衡,岂非寒天下文士之心?
“高福,”皇帝于延英殿独坐,指尖轻叩御案,声音带着不容置疑的威压,“去查查,此番弹劾,源头何在?那李亿,在其中又扮演了什么角色。”
“老奴遵旨。”侍立一旁的内侍监高福躬身领命。
不过数日,一份密报便呈于御前。高福低声道:“陛下,据查,最初联名上奏的几位御史,其中两人与吏部徐侍郎过往甚密,而徐侍郎……此前因柳氏之事,对鱼玄机心存芥蒂。李亿李主事,虽未直接出面,但弹劾札子中所引‘狂悖’诗句,经查证,并非全然出自《西行漫记》正本,似有添改、仿作之嫌,来源……指向李亿,以及李府一名唤石榴的婢女。”
皇帝听完,嘴角掠过一丝冷峭的笑意。果然如此。徐侍郎挟怨报复,李亿顺水推舟,意图逼那鱼玄机重回其掌控。内帷争斗,竟敢攀扯朝局,利用御史言路以遂私欲,此风绝不可长!
“徐子显……”皇帝沉吟片刻,“此人器量狭小,不堪大用。寻个由头,外放了吧,让他去张掖做个司马,磨磨性子。”
“至于李亿……”皇帝目光深邃,“此子倒是心思缜密,懂得借力。只是,格局小了些,过于执着于私欲。念在其状元之才,着他……兼领校书郎一职,去翰林院整理三年前河西战事的档案文书,那些军需粮草账目最为繁琐,让他静静心,也好好想想,何为臣子本分。”
“奴婢明白,即刻去传旨。”高福躬身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