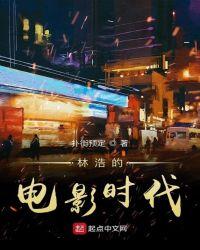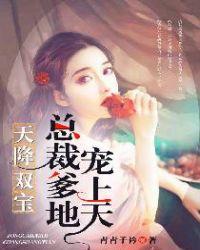52小说网>炽年长明 > 夏(第1页)
夏(第1页)
春末夏初的气息愈发浓郁,昆城的白昼变得绵长。耿星语坐在书桌前,空气中似乎还隐约飘散着墨锭研磨开后特有的松烟清香。
面前摊开的不是数学习题,而是一张被她写写画画了很多遍的、关于未来一年规划的草稿,旁边还搁着一支小楷笔,笔尖的墨迹已干。
窗台上的绿萝藤蔓垂坠而下,绿意盎然,一如她心中那个经过无数个静心书写、反复斟酌后,愈发清晰和坚定的念头。
这个决定,并非在躁动中产生,而是在日复一日逐渐沉淀下来的清醒认知。她比任何人都清楚,书法这条路,讲究的是水到渠成,是厚积薄发。
之前的动荡、休学、治疗,不仅打断了文化课的进程,更严重的是中断了她需要日日不缀、悉心涵养的笔下功夫。
那些落下的,不仅仅是知识点,更是手腕的稳定、对笔墨精微的控制力,以及沉浸在黑白世界里所需的那份纯粹心性。
以她目前恢复练习后的水准,去应对顶尖美术学院的书法专业考试,她知道,火候还差得远。
而另一个更深沉的驱动力,如同笔下暗藏的力道,源于对未来的勾勒。
那个未来里,不只有她倾心的翰墨书香,还有一个鲜明温暖的身影——黎予。
她不再满足于精神上的遥相呼应,她渴望的是地理上的靠近,是能更频繁地分享同一片江南的烟雨,是能在她想念的时候,一张高铁票就能触碰到真实的温度。
深思熟虑,在一个两人刚结束一日课业、氛围宁静的晚间视频通话里,耿星语轻轻放下手中正在把玩的一方青田石素章,将这个重要的决定,慎重地铺陈在黎予面前。
“黎予,”她的声音带着书法生特有的沉静,却又比平时多了一份决断的力度,“有件事,我考虑了很久,想和你商量一下。”
屏幕那头的黎予似乎刚画完草图,指尖还沾着点炭灰,闻言立刻抬起头,将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凑近屏幕,眼神里满是专注:
“嗯?什么事?你说。”
“我……”耿星语的语气平稳而清晰,“我打算复读一年。”
黎予微微睁大了眼睛,脸上掠过一丝讶异,但没有出声打断,只是用眼神鼓励她继续说下去。
“我已经准备好再复读一年了。”耿星语继续说道,坦诚着自己的评估,“不仅仅是文化课,更重要的是手上的功夫。之前统考的成绩不是很理想。书法这东西,骗不了人,落下了就是落下了,需要时间重新捡起来,而且想冲顶尖的学校,现在的积累还远远不够。”
她抬起眼,眸光清亮而坚定,“我不想将就。所以,我已经在准备重新参加艺考了。而且,目标也不再是之前考虑的川美。”
她停顿了一下,仿佛在积蓄力量,然后清晰地说出了那个承载了更多重量和期望的名字:“我想考国美的书法系。”
国美。这不仅是中国艺术教育的顶尖殿堂,其书法专业更是底蕴深厚,名家辈出。
更重要的是,它坐落在杭城——一个与黎予所在的沪城,同处于长三角核心圈,高铁穿梭便捷,几乎可以算是“同城”的距离。更好的学术氛围,更高的艺术平台,以及,触手可及的相聚。
然而,追求更高的艺术境界,也意味着需要投入更漫长的准备期。
耿星语没有回避这个现实问题,她的眼神里带着一丝坦诚的考量:
“这意味着……如果我决定复读,并且目标是国美书法系,我们可能……还需要异地更长的时间。不是之前预估的几个月,很可能是一年,甚至,如果第一年结果不理想,可能需要更久。”
她说完了,静静地看着屏幕里的黎予,等待着她的反应。这不仅仅是一个关于学业和职业路径的抉择,更是一个直接影响她们未来相处时光的重要议题。
黎予在短暂的沉默中,迅速消化着这个信息。她的目光掠过耿星语身后书架上那一排排整齐的法帖和卷起的宣纸,最终落回耿星语脸上。
她没有先去计算那“更长异地”的时间,而是首先看到了耿星语眼中那簇对于书法艺术本身不容置疑的虔诚与热爱,以及那份不愿亵渎这门古老艺术、定要登堂入室的决心。
几秒钟后,黎予的脸上重新绽放出笑容,那笑容如同冲破云层的阳光,温暖而充满力量,不带一丝阴霾。
“我当是什么大事呢!”她的语气甚至带着点如释重负的轻快,“看你那么严肃,吓我一跳。”
她身体前倾,双手交叠垫在下巴下,眼睛像蕴藏着星星,无比认真地看着耿星语:
“没有任何事情,比你自己的人生追求,比你想成为什么样的艺术家,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