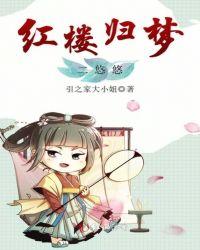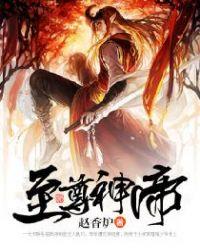52小说网>谢尽欢鸣龙小说TXT全集免费阅读 > 第三十四章 情不自禁(第1页)
第三十四章 情不自禁(第1页)
轰隆隆……
闷雷阵阵,滂沱大雨砸在楼船甲板之上,噼啪作响。
楼船乘风破浪,在北冥湖之上遨游,一袭金甲的白毛船长,双手叉腰站在桅横杆之上,眼神灼灼。
南宫烨等人,则在船只各处朝着四方打。。。
雪落无声,屋内炉火噼啪作响,映得谢尽欢眉目温润。
他伸手轻抚窗棂上那朵凝结的雪花,指尖微凉,心却滚烫。
那一瞬的静谧,仿佛天地屏息,只为容纳这一声低语与一片雪的相遇。
他没有等回答??也不需要回答。
自那日心渊崩塌、新誓立成之后,世界并未骤然清明,也未彻底安宁。
旧习难改,人心易惑。
香火虽熄,信仰的惯性仍在暗处流淌。
有些村庄仍将“鸣龙”
二字刻于门楣,用以驱邪;有些宗门借“心语者血脉”
之名,收徒敛财,妄称能通神谕;更有边陲小国奉《伪誓录》为国典,以“净化心灵”
为由,禁绝悲喜,强制百姓每日诵经三遍,违者视为“心魔”
。
可与此同时,北冥湖畔的心语学院已扩至七院,南北东西中各设分堂,连西域沙民、南岭蛮族也遣子弟前来求学。
他们不拜神像,不念咒文,只学如何倾听??听风,听雨,听邻人呼吸中的焦虑,听自己心底未曾说出的呐喊。
小彪在来信中写道:“共感非天赋,乃责任。
听得见,便不能装作不知。”
谢尽欢将手稿收入柜中,起身添柴。
火光跃动间,忽觉胸口一热。
不是契约的震颤,也不是骨笛残魂的共鸣,而是一种更为熟悉的暖意??像是有人在他心湖投下一颗石子,涟漪缓缓荡开。
他怔住。
片刻后,门外传来极轻的脚步声,踏雪无痕,却带着某种节奏,像极了幼时母亲哼唱的安眠曲。
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寒风卷着雪粒扑入,旋即又被一道无形屏障挡下。
一个身影站在门口,披着灰袍,身形瘦小,脸上覆着半透明的雾纱,唯有一双眼睛清澈如泉。
“谢叔。”
那孩子开口,声音稚嫩却不怯懦,“我……听见您了。”
谢尽欢蹲下身,平视着他:“你从哪儿来?”
“南沼。”
孩子说,“我娘死前说,若我能听见‘风里的哭声’,就来找您。
她说您会告诉我,为什么我会疼别人的疼。”
谢尽欢心头微颤。
这是典型的“初觉醒者”
??尚未受训,便已被动承受他人情绪的孩子。
这类孩童极易精神崩溃,或被邪教掳走,炼成“怨灵容器”
。